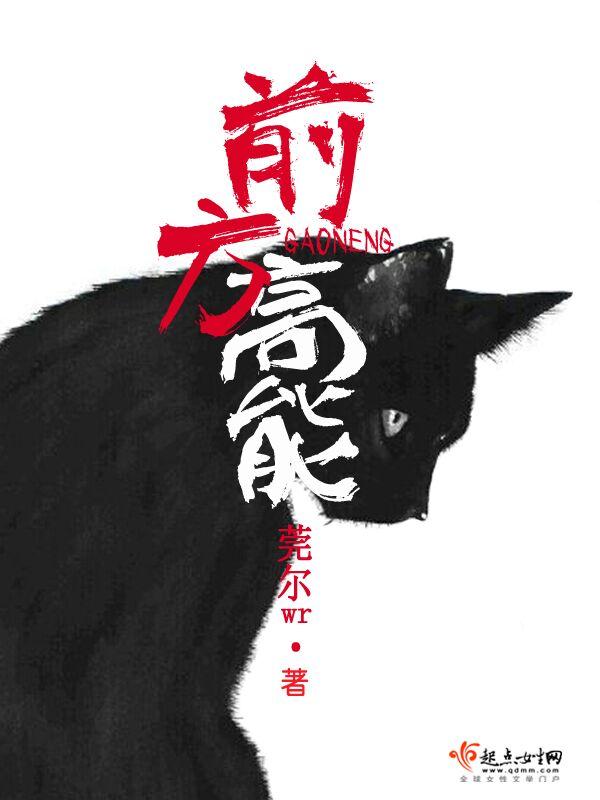吞噬小说网>徐则臣北上所有人物 > 宝马宝马(第2页)
宝马宝马(第2页)
沙袖说:“那你为什么现在不让她把你送到小区门口?”
“我不是已经说了吗,觉得拐到这边让人家麻烦,也担心你看了多心。”
“就这么简单?”
“这还不够?”
“那个女人喜欢你,”沙袖说着就哭了,“她看你的眼神有问题。”
“哪有什么问题?”一明无辜地看着我和老边,两只手摊开来给我们看,好像问题在手心里,“我怎么不知道?”
“我说有问题就有问题。她的眼神就不对!”
女人这方面的直觉远胜过男人。我和老边劝一明,以后少和她来往就是了,你没问题也得防着别人有问题。边红旗暗示他赶快认输,他在这方面有心得,和女人要想和平共处,必须时刻记住,她说什么就是什么,有意见下次提。一明是个老实人,就老老实实按照边红旗的意思低头了,向我们大家保证,以后决不再坐那个女学生的宝马了。
此后的一周风平浪静,各种迹象都表明,宝马事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。我们生活如常,唯一动**的是边红旗,风声越来越紧,他不得不深居简出。一天的大半时间都在**度过,偶尔沈丹也会过来,他就更下不了床了。他把房间里的所有与假证有关的东西都转移走了,他说是为了我们三个的安全考虑,防患于未然,省得到时候连累我们。除了沈丹和食物,他不再往家里带任何东西。沙袖对老边带女人回来不太高兴,原因是沈丹的叫声常常不能自禁,关两道门她的声音依然保持了强劲的穿透力,搞得我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把耳机带上。
没想到沙袖的耐力和认真如此惊人,她在两周后把一明堵在了宝马边上。在硅谷前面,一明刚从车里出来,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人,一声不吭地盯着他。车上的女学生摁着喇叭让她避开,沙袖动都不动。
女学生把脑袋伸出来问一明:“她是谁?”
沙袖说:“他老婆。”
一明说:“你怎么来了?”
沙袖说:“回家说。”
一路上沙袖都没说话,默默地流眼泪,一直流到家里还在流。一明跟在后面解释,怎么解释都没用。一明后来对我说,真的没有什么,至少他没对那个女人动过歪心思。他已经找借口推辞了,但是女学生盛情难却,他是个男人,总不能告诉她说为了避免老婆生疑吧?但是沙袖不听,她说只要想推辞,怎么可能找不到理由呢。沙袖也有道理,除了死亡,还有什么拒绝不了的呢?
出了事一明就找我,希望我能为他开脱一点儿。他以为沙袖会大吵大闹,进了门他就对我打手势递眼色,让我出来,看那样子我就知道出大事了。
沙袖只是安静地淌眼泪,没有弄出任何大动静。一明却是手脚并用去解释,脸都涨红了,他的脸一红就像已经做了亏心事。一明说:“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?不信你问穆鱼。”
我只好说:“一明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们同学四年,上下铺的兄弟,我知道的。”我正准备把大学里一明洁身自好的证据再次拿出来,沙袖打断了我。她的声音很平静,听起来和哗啦哗啦的眼泪没什么关系。
沙袖说:“其实你们有什么我又能怎样?在这里我就是个废人,我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都做不来,一个人活下去都成问题,我凭什么要求你那么多?随你,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”
说完抹一把眼泪就回房间了。一明和我都愣在那里,感觉像是攒足了力气的一个拳头准备打出去,突然发现对方只是一团棉花。失重感让我们俩大眼瞪小眼,不知该怎么办。边红旗从房间里伸出头,问我们出了什么事,看了一明沮丧的脸立刻明白了,招招手小声说:“又出问题了?什么事告诉我,我帮你搞定。对付女人我还是有一套的。”
没等一明把事说清楚,沈丹就在边红旗的房间里叫他。老边说:“过会儿再说,我先把这边的事解决了。”脑袋缩进去,门也关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