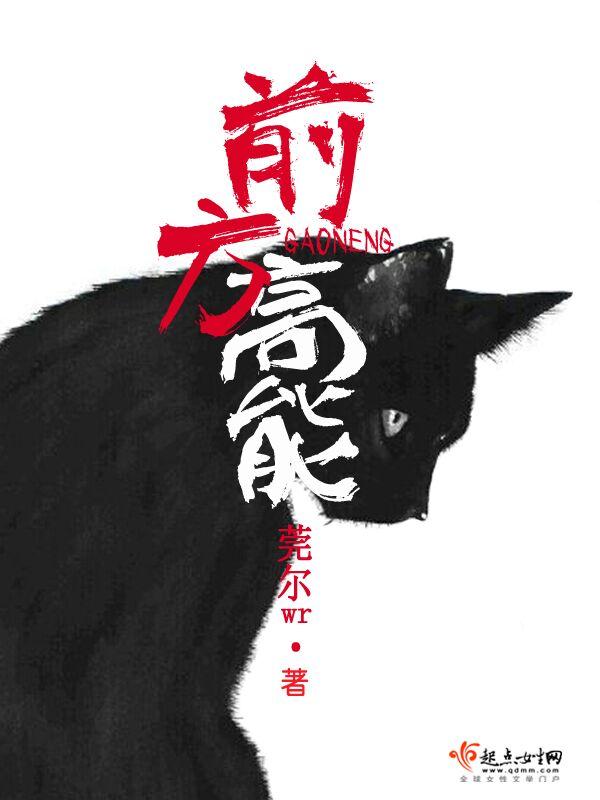吞噬小说网>徐则臣北上所有人物 > 6(第2页)
6(第2页)
“说什么?”
“我想那个,就那个,追她?”
“没有。”
“没说啊?哦,没说好。”
他都有点儿抓耳挠腮了,不停地用右手里的一本杂志样的东西敲打左手。康博斯拿过来看了看,是《诗刊》杂志,翻了一页,在目录里看到班迁的名字,上面印着:班迁诗三首。
“快看快看,”康博斯对着佳丽喊起来,“小号的诗在《诗刊》上发表了,一口气就是三首。”
佳丽拿到杂志,找到刊载小号诗歌的那页。“果然是三首!小号,就是因为这个喜事请我们喝咖啡的吧?”
“不是。是。我出门时刚收到的。”
“靠,小号,你到底想说什么?”
小号更窘了,手不知往哪儿放,总算找到了口袋,摸了一下叫起来:“哎呀,还有五香鸡胗,差点儿给忘了。佳丽,给你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,和过去的很多次一样,他给佳丽带了一小袋五香鸡胗。
康博斯说:“小号真是个有心人哪,嫁这种男人放心。”
佳丽好像没听见康博斯在说什么,一边吃鸡胗一边看小号的诗,嘴里念叨“不错,嗯,不错”,不知道说的是小号的诗不错还是鸡胗不错。不管是哪个,小号都很开心。
他们一路说诗,穿过北大校园往蓝旗营走。在路上康博斯拍小号马屁,康博斯说,小号这下玩大了,上《诗刊》了,马上就大师了。佳丽问,是不是《诗刊》很难上?那当然,康博斯说,容易上我也上了,可惜整了二十多年也没整上去,绝望之下就不再写诗了。还有啊,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诗人吗,数不过来,据说快赶上“诗歌大跃进”时的数量了,全民皆诗人,当然我们俩除外。你想想,这么多诗人,真正能在《诗刊》上露脸的才几个?我们小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,你看看,排在这个栏目第三号的位置,头两个都是名家,成名半辈子了。佳丽惊叹,不得了小号,一下子成著名诗人了。今晚的咖啡一定要喝,得痛痛快快地当白开水一样喝。他们的拍马屁和玩笑听得小号的心揪起来,一惊一乍地跳,不过感觉还是相当好。
快到蓝旗营时,他们在一座天桥底下看到一个街头艺术家。一个老头儿,应该说是个书法家,在路灯底下铺开毛边纸弓着腰写字,毛边纸下面是一块破旧的毡子,用了很多年了,已经脏得不成样子。旁边是一辆三轮车,车厢上放了一块大木板,堆着一大包用床单似的布包裹起来的东西,车把上挂着一个蛇皮手提袋,袋子里是一个热水瓶。地上摆了一摊写过毛笔字的白宣纸,四角都用小砖头块压着,是他的作品。真草隶篆都有,写得还不错,尤其是临摹毛泽东的狂草的那幅,虽然不太像,但是绕来绕去颇有些气势。他们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,老头儿根本不理会他们的存在,只顾提着大笔在毛边纸上转,一会儿一个淋漓酣畅的篆字就转出来了。
“艺术家,”离开了天桥佳丽说,“跟小号一样。让人肃然起敬。”
康博斯说:“小号,什么时候也到街头来作诗。听说很多诗人都到地铁站里赚钱,现场写诗,现场卖。”
“我不行。”小号连连摆手,“我写得慢。街头艺术家需要勇气,我倒是挺羡慕这样的生活和写作。”
“让你也来做街头艺术家,你干不干?”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接着他们又争论了一通,就是这样的街头艺术家和诗人,他们搞的到底是艺术还是行为艺术,佳丽也掺和进来。大家都没说出个道道来就到了万圣书园。找了一个小桌子坐下,壁灯温暖幽暗,旁边很多都是扎辫子的艺术家,头凑在一起说话,都像在密谋。
“有点儿意思,”佳丽觉得很不错,“这地方我还是头一次来。”
小号也是第一次。事实上咖啡馆他也是第一次进,尽管之前他已经打听了相关的价格,真正坐下了心里还是没底。服务员拿着茶单上来时,他歪着头小声问康博斯带没带钱,他担心身上的钱不够。康博斯让他放心,只管放开了请佳丽喝。小号略略放了心,打开茶单还是吓了一跳,一杯可乐的价格都让他心里发疼,觉得这么长时间不进咖啡馆是对的,进了说不定会更后悔。佳丽点了热牛奶,康博斯点了红茶,小号狠狠心点了咖啡,不喝咖啡算什么进咖啡馆呢。
三个人抱着杯子边喝边聊,小号才逐渐放松下来。康博斯暗示小号,该出手时就出手,该说的话想办法一点点说出来。本来放松下来的小号,一接到康博斯的暗示就又开始紧张了,下意识地就到额头上擦汗,偏偏佳丽就坐他对面,抬头看见低头也看见。康博斯干脆不再对他发信号。其后每个人又要了一杯,还要了一份爆米花,一直坐到了十一点。买单的时候小号对康博斯说,看来小资的日子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过的。康博斯说,是啊,所以小资才成为很多人的生活目标。
回去的路上经过天桥,他们又看见了那个街头艺术家,他已经睡着了。地上的东西已经收起来了,他就睡在车厢上的大木板上,当时他们看到的一大包东西是被褥。书法家只露着一个脑袋,整个人蜷缩在被子里,不知道他冷不冷。三步以外的马路上车来车往,他睡得很沉。夜风吹过来,挂在车把上的水瓶摇摇晃晃。
“他就睡这儿?”佳丽大概觉得一个艺术家不应该遭受这种待遇。
“我也睡过街头,”小号说,“刚来北京的时候,还不如他,连被褥都没有,也没有热水。”
“为了艺术露宿街头。”佳丽还是忍不住感叹。
康博斯问小号:“你能为了诗歌露宿北京街头吗?”
“我为什么要为诗歌露宿街头?如果仅仅是写诗,我待在家里种两亩地照样写,还来北京干吗?”
“那你来北京干吗?”
“生活。像别人一样过好日子。”
小号在说实话。康博斯看看佳丽,她不说话。大家都清楚,对他们三个人来说,在北京或者想留在北京的目的本质上是相同的,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。其他人不也是如此吗?有一会儿三个人都不说话,安安静静地向前走,都不免有些伤感,觉得这些年疲于奔命其实挺可笑的,不过是为了待在这个地方。在这儿过上好日子了吗?不好说,在很多时候盘旋在内心和理想里的,并不是什么美好的生活,而是“北京”这个地名。首都,中国的中心、心脏,成就事业的最好去处,好像待在这里就是待在了所有地方的最高处,待在了这里一切都有了可能。而可能在哪里,大家都不去想了,或者不敢去想,因为你要待在北京。
快到北大东门时,迎面过来一个卖玫瑰花的小姑娘,见着康博斯就盯紧了,让他买一朵花送给佳丽。康博斯想避开,说什么也不行,那训练有素的小姑娘就认定康博斯是佳丽的男朋友。康博斯觉得再推会让佳丽很没面子,就买了三枝,买的时候说,小号,这是我们俩共同送给佳丽同志的玫瑰。祝佳丽越来越漂亮。他付钱的时候把玫瑰花递给小号,让小号送给佳丽,心想,看你的了。他以为小号会借花献佛表达一下自己,至少说一句暧昧的,比如“送给你”。没想到小号拿到花脸就红了,送给佳丽的时候把康博斯的话又重复了一遍:“这是我们俩一起送给你的。”
康博斯绝望地拍拍小号的胖肩膀,“班小号,你让我无话可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