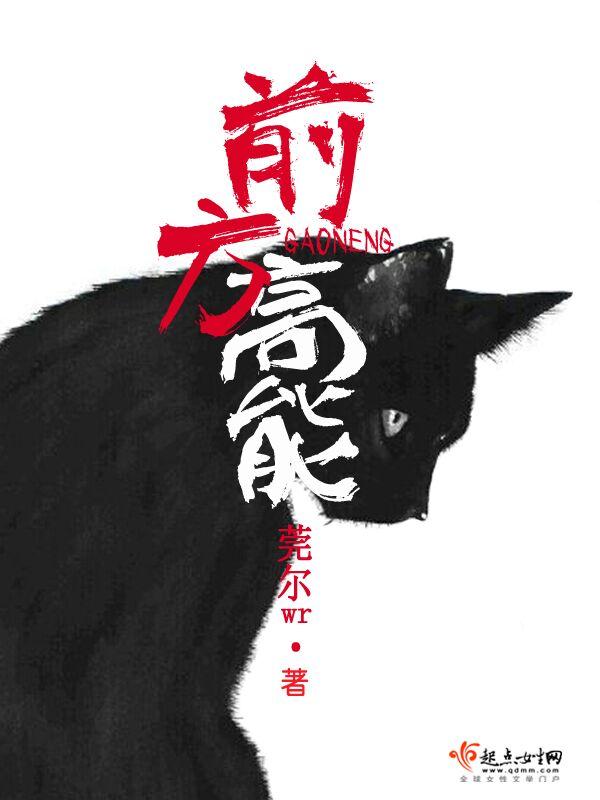吞噬小说网>可我是天才 > 八 滚烫的额头(第2页)
八 滚烫的额头(第2页)
福恩今天倒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,话说回来,他从来就没有开心过,永远像是刚刚跟人闹过别扭,满脸的愤愤不平。
难道他的病症之一就是不合群、愤怒?
我的注意力被困在这个地方了,犹豫再三,我决定试探一下福恩:你……也是RETT吗?
他就跟没听见一样。这家伙!算了吧,就当我没说。
一碗饭快吃完了,福恩突然指了指自己,说:听说过瓦解性精神障碍吗?
我大吃一惊,拼命摇头。我唯一知道的病就是RETT,我还以为这里的人全都是RETT呢。
也许是为了安慰他,我主动告诉他,我是一名RETT,我会一天天退化,一直退到零。
福恩又不作声了。
悲惨处境(虽然是假的)得不到同情,我很失望。正要离开,福恩望着碗里的饭粒嘀咕了一句:其实,过了儿童期,每个人都在一天天退化,正如人一出生,就在一天天走向死亡一样。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真理。
哇!你说话像个思想家。
这不是我说的,是我妈妈妈说的。
你妈妈不对,因为人可以学习,学习可以让人进步。
那正是人们想出来的抵抗退化的手段,而且,所谓学习,也只是重温和消化前人的发现而已,真正有创见的人十分罕见。
对对对……这话弓丨起了我的共鸣,正要跟他继续讨论,他站起身来,拔腿就走。
他要是随和一点就好了,我们说不定可以成为最好最好的好朋友,他现在这个样子,我实在没法走近他。又一想,如果是那个瓦解性精神障碍导致的,我就不该知难而退,而应该张开双臂主动向他走去。
很快我就开始厌倦了。季老师上一节课,我要训练一个星期。一般来说,剩饭炒到第三天,我就没了兴趣。那些字,那些故事,不再面向我,而是无聊地背向我,丝毫不再让我激动。我猜它们对我也失去了初交见面的兴趣,有时,我读着读着,突然打出一个长长的呵欠。
有一次,正当我被呵欠折磨得泪花滚滚时,卢园长过来了。
稍微表扬你一下,你就骄傲了是吧?卢园长语气很重,但眼睛还是眯着的,说明她并没有真的生气。
我告诉她,只有背诵新的东西,我才不会打呵欠,背过的东西再背,就像把嚼过的饭吐出来,再吃下去。
这个比方不赖。她说:不过,毕竟不是吃饭,所以,就算是背得要吐,你还是得背,直到达到季老师的要求为止。
她让我去把字典拿来,她要开始考我了。她常常出其不意地闯进来考我。
她随手点了一个字,喊了声开始。
背了一阵,我就开始磕磕巴巴,中间几次完全接不上来。卢园长不得不提醒我,提醒到第四次时,她一扬手,把字典重重地砸在桌上。
搞什么名堂!第一次都比今天背得好,这周已经过去三天了,不仅没有进步,反而后退了这么多,说,什么原因?
我每天都在读,都在背,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。
卢园长的眼睛渐渐变成了寒光闪闪的三角形。
压力之下,我突然为自己想到了一个比方:就像在水池里网小鱼,第一网下去,可以舀很多鱼,因为鱼没有防备,第二次,第三次,鱼越来越少,因为它们都有了经验,知道该怎么逃了。
闭嘴!就你爱顶嘴!卢园长突然压低声音:知道你为什么爱顶嘴吗,你无非是0视甚高,告诉你,在我这里,你不过是个RETT,你跟他们毫无区别。
可是,我来的时候就告诉过你了,我不是……
不是什么?卢园长的目光突然冷冷地逼向我。我明白了,我不能说那句话,我不能让大家知道我是撒了谎进来的。
开始吧,季老师叫你怎么做,你就怎么做。明天这个时候,我再来考你。卢园长把字典重重地塞到我怀里。
我得到允许,可以到我喜欢的地方用我喜欢的任何姿势去背字典。
我夹着字典,来到外面,太阳晒在我刚刚挨过训的沮丧的身体上,温暖得让人想哭。我往小树林那边走去。
果然,我看见福恩的画架了,不过,福恩却不知道在哪里。
我走过去看了看他的画,还是线条画,不过他的线条越来越熟练了,他画的直线,比我用直尺画出来的还要直,曲线光滑圆润,像崭新的丝线。我就是搞不懂,他是怎么用线条把藏在画纸下面的物体表现出来的,虽然他画了一些线条,但实际上他画了三样东西:线条,线条下的物体,以及被物体破坏了形状的线条。而稍稍站开一点,其实只能看到一样东西,就是那个并不存在的物体,真是太神奇了。
别看了,你学不会的。
福恩的声音在我脚边响起。
他躺在草丛里,身上盖着一束树枝,我走过来时,竟没发现他。
我问他一天画几幅,他说他高兴时一天画好几幅,但他会把它们都藏起来,只留一张给他们看。当他不高兴时,一笔也不画,但他会从藏起来的那些画里抽一张出来应付他们。
把你的字典给我看看。福恩伸出手,我把字典递给躺在地上的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