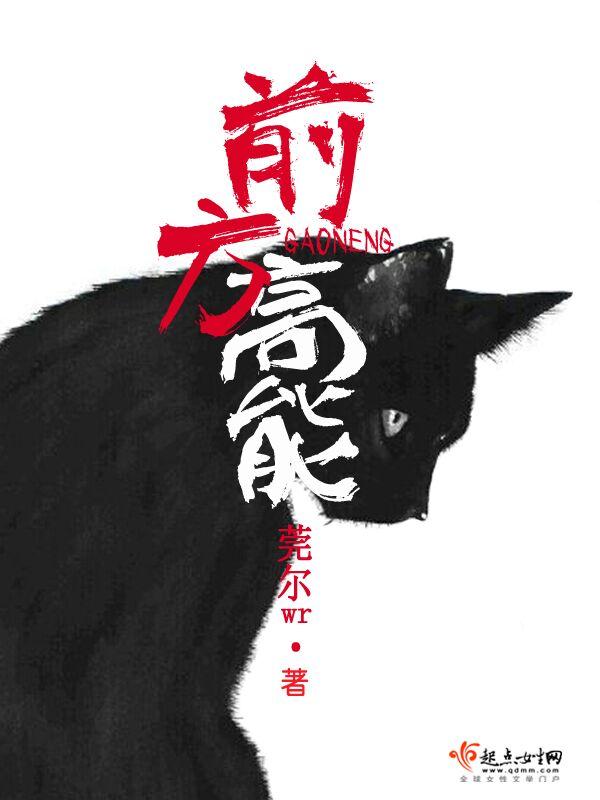吞噬小说网>大宋第一状元郎 最新章节 无弹窗 > 第51章 苏湄请行(第2页)
第51章 苏湄请行(第2页)
她顿了顿,深吸一口气,像是下了很大决心:
“恳请公子允我随行北上,一路学习请教农技实务。他日若有所得,或可传于乡里,助农人增产,解百姓饥困。”
理由冠冕堂皇,语气诚恳真挚。
但章衡听出了不对劲。
太正式了,太像背书了。而且时机太巧——早不来晚不来,偏偏在他要动身的时候来。还有那身打扮,那利落的举止,那鼓鼓囊囊的包袱……
他下意识看向苏颂。
苏颂站在廊下,背着手,眼睛看着远处城门的方向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但章衡注意到,老头的左手在袖子里微微动了一下——那是他思考时无意识的小动作。
章衡心里明白了七八分。
这不是简单的“求学”。
至少不全是。
“苏姑娘,”他斟酌着开口,“北上路途遥远,凶险难测。且我此行是为科考,并非游学,恐怕……”
“湄不怕苦。”苏湄打断他,声音还是清脆,但多了点执拗,“农技实务,正需跋山涉水、亲历亲为。公子教人挖沟,湄可帮公子记沟渠深浅;公子教人施肥,湄可帮公子算肥力配比。至于科考——”她忽然笑了笑,笑容里带点狡黠,“湄虽不能入场应试,但在外为公子研墨铺纸、打理行装,总还是做得的。”
这话说得滴水不漏,既表明了“有用”,又放低了姿态。
章衡一时不知怎么接。
他再次看向苏颂。
这次苏颂终于转过脸来,看着他,缓缓开口:“湄儿自幼随她舅父行走运河,熟悉水路码头。她母亲去得早,我又常年在外为官,这丫头野惯了,寻常闺阁拘不住她。”
话说得很平淡,但章衡听懂了弦外之音。
——这丫头不是普通闺秀,能应付江湖事。
——她熟悉水路,北上要走运河,用得着。
——她“野惯了”,意思是能吃苦,不娇气。
还有更深的一层:苏颂让自己的女儿跟着他,既是帮忙,也是……某种程度的托付,或者说,绑定。
章衡沉默了片刻。
他脑子里飞快转着:苏湄的出现太突然,但仔细想,又合情合理。钱塘刺杀之后,苏颂不可能放心让他一个人上路。派护卫太显眼,派心腹又可能暴露。女儿这个身份最灵活——既是自己人,又不会引起太多怀疑。而且女子身份在某些时候反而是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