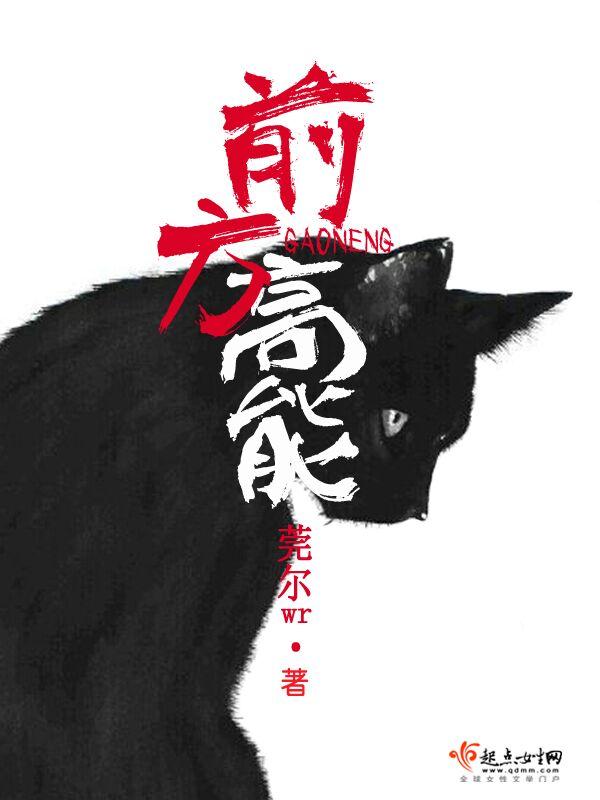吞噬小说网>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剧情简介电视猫 > 第四章 初遇强敌(第3页)
第四章 初遇强敌(第3页)
“都这种时候了大人您还避什么嫌?装着与你无关人家就不怀疑你了?”对于他的抱怨,秦师爷先是不客气地甩了一句,随后又安慰道,“大战刚过,世子重伤,老王爷在北境且还腾不出手呢。您放心吧,我这次离京,大人把府上最得用的人全派了出来,从北境过来的所有要道我都放了眼线。长林是军将之府,能有什么懂得隐藏行迹暗中查访的人?就算他北境的动作真有那么快,咱们也能提前知道,加以防备。”
这一番话软硬兼施,总算稍许安稳了张府尹惊惶忐忑的心。然而令他失望的是,即便是这样暴风骤雨,近乎破罐子破摔的行动,效果似乎也不比他前些日子更强。三天过去了,四名人证依然踪影皆无,连个靠谱的线索都没有找到。
入冬后日落的时辰更早,晚膳刚过,天色便已透黑。
林奚并没有邀请萧平旌在扶风堂暂住,这位长林二公子也根本不需要人家邀请。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就是他的落脚点,霍掌柜也自顾自地去给他收拾了一套舒适的客房出来,两个人谁也没想过是否应该先问林奚一声。
云大娘倒是过来问了,她问的是:“不知二公子喜欢吃些什么?”
眼下这样的情形,即便没有师命,赶他出去也不合情理,已经有些头疼的林奚最终只能一言不发。
吃过晚饭,萧平旌先睡了一个多时辰,起来自己打水洗了脸,换了一身全黑的夜行衣和软底小靴,将长剑束在背后,悄无声息地自药圃后门离开。
夜空中不见月色,只有繁星点点。城内夜间例常的巡防在萧平旌眼中满是漏洞,轻易便规避开来,翻入了府衙的后墙。
大同府衙和其他官宅的布局基本一样,前衙后宅,外加一个花园和一处书楼。张庆庾的书房跟随主流设置,被放在了东南院紧邻花园之处。
又是一整日无果的搜捕,这位府台大人自觉疲惫已极,但又升不起一丝睡意,上床躺了一会儿,又爬起来把秦师爷叫到书房商议。
比起初到大同时的满怀信心,秦师爷现在的心情也有些阴沉。碍于他背后的情面,张庆庾跟他说话的音调依然客气,但话里话外都难免透出一股责备之意。
秦师爷没有为自己多加辩解,只是问道:“这种搜法都找不到人,实在不同寻常,他们会不会已经逃出大同府地界了?”
张庆庾立即否认,“不可能,我当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锁全境。据说那个船老大腿上还有些轻伤,他们若是向外逃,到不了府界就被能被钱参领追上抓住了,只可能是潜回了城中,想等风声过去。”
秦师爷紧皱双眉,“可本地跟他们沾亲带故的人都已经通查了一遍,并无丝毫可疑的迹象。如果没有熟人相帮,他们到底还能怎么隐藏?”
张庆庾咬了咬牙,情绪突然有些失控,“你问我我问谁去?天子御使想来已经出京,北境的人说不定过几天也就到了。咱们的时间眼看越来越少,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不成?”
秦师爷冷冷地瞟了他一眼,道:“府台大人,现在不过是走脱了几个人证而已,可回旋的余地还多着呢,此刻就说坐以待毙,早了些吧?”
张庆庾粗粗地喘着气,没有说话,室内随之沉寂下来,气氛有些凝滞。
此时已近子夜,府衙各处除了巡夜值守的灯笼外,唯有书房这一处光亮。萧平旌矮身踩着墙头查看了一圈,自然而然向这边疾行而来。
院落中有株垂柳,萧平旌的足尖在院中树梢上轻点借力,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南侧的檐角上。
主屋内的秦师爷突然眼神一凝,站了起来。
张庆庾抬头问道,“你想到什么了?”
萧平旌踩着青瓦,向后窗方向多走了两步,步履轻盈,几无声响。
秦师爷的唇边却微起冷意,手腕一翻,握住桌上的铜枝烛台,运力向上掷出。烛台直冲萧平旌脚下的屋顶,瓦片飞溅。
萧平旌猝不及防,拼力后跃,险险才避过这一击。
向上出手的同时,秦师爷身如利箭,自窗口一跃而出,在檐上的萧平旌立足未稳时,当头一掌劈下,掌风之凌厉,令这位学艺琅琊的年轻人都吃了一惊,匆忙间虽然避开,但肩部被掌风所扫,踉跄退了一步,才拔出背后的长剑。
短短片刻,两人在檐面上快速交手了数招,一时无人能占上风,各自的心头都甚感诧异。
这时张庆庾已从室内奔出,狂呼道:“刺客!抓刺客!”
院外值守的侍卫闻声涌了过来,萧平旌眉头一皱,不敢恋战,急攻了两剑,撤身向外院奔去。
秦师爷紧追在后,眼见前方就是外墙,不由脸色一沉,飞身踏在下方侍卫的肩头,同时捞过一把长枪,运力向前飞掷而出。
萧平旌听到背后破空之声,跃身而起,足底借势在枪杆处一踏,反倒翻身上了高墙,快速消失于夜色之中。
秦师爷心知追赶不及,停了下来,自言自语地赞了一声,“真是好身法。”
张庆庾过了好一阵才仓皇赶了过来,颤声问道:“秦师爷……那……那是……”
秦师爷冷冷道:“如此高手,想必是北境的人。”
张庆庾瞬间面色如土,失声道:“你不是说,长林王爷还腾不出手,你也有眼线可以提前察觉吗?”
秦师爷眯起了眼睛,似在跟他说话,又似在自语,“长林麾下多是军旅之人,按理确实不应该这么快……这个年轻人,他究竟会是谁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