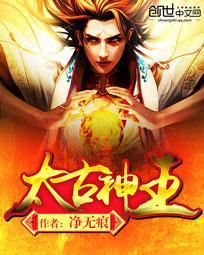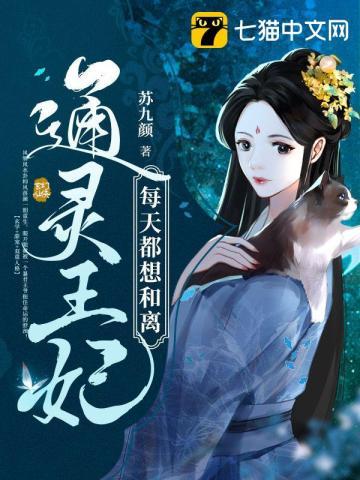吞噬小说网>天幕直播我是秦三世最新章节免费观看 > 第45章垂拱而治(第2页)
第45章垂拱而治(第2页)
<幸好秦怀帝是实权帝王,而且在位期间对军权的掌控也没有鬆手,要不然非得出事不可。>
惠施胳膊肘捅捅庄子:“看!这位居然是偏向你们道家的君王。”
他都垂拱而治了,不是道家是什么?
庄子短暂的思索了一下,然后道:“也行。”
惠施:“?”
“你要不要那么平静?这可是君王倾向道家!放在平时,你怕不是要感嘆一句『得遇明主?”
庄子瞥了他一眼,那眼神仿佛在说“你还是太执著於表象了”。他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衣袖,虽然此刻他们可能只是意识体或投影,但这並不妨碍庄周保持他的风度。
“明主与否,非看其言,更观其行,察其势。”庄子缓缓道,“垂拱而治,听起来是无为,实则是『无不为之前提。
国家机器若能自行良好运转,如溪水匯入江河,自然奔流,君王又何须事必躬亲,徒劳心神?”
庄子条理清晰:“你看此秦,法度森严,吏治虽有蠹虫,然框架已成,如臂使指。
此时君王若能把握大势,知人善任,减少不必要的干预,让民力得以休养,让万物得以自化,这便是『道法自然的一种体现了。”
春秋战国大爭之世根本就宣扬不开道家,这也是庄子淡成那样的原因之一。
不是不到,时候未到。
至於那些拿著道家理论,和法家儒家一样必定要为自己的思想爭夺一席之地的弟子?
个人选择不同。
庄子向来是能支持的就儘量支持,支持不了的隨他去吧。
惠施喃喃自语:“挺有道道理的……不过垂拱而治不適合大爭之世不假,可是如果操作得当,也未必不能富国强民。”
庄周:“这不好把握。”
都知道垂拱而治最能恢復国家生態,尤其是在战后。但这玩意好把控吗?
这需要极高的把控力,既要放得开,又要收得住。放,易生权臣;收,又回到事必躬亲的老路。
这其中尺度,堪比钢丝行走。
庄周自己自信能够把控,可是又有多少君王愿意卸权?
就拿大秦现如今在他们面前的这几位主,哪个是愿意卸权的主?
列国臣子中,法家如商鞅、韩非等人,对“垂拱而治”颇不以为然,认为这削弱了君权,易生祸乱。
儒家则觉得这太过消极,君王当“仁政爱民”,积极有为。
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,庄子点出了一个关键——任何治国理论,其有效性高度依赖於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国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