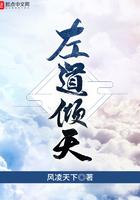吞噬小说网>1848大清烧炭工起点中文网 > 第372章 临门一脚(第2页)
第372章 临门一脚(第2页)
咸丰把关外的马队,以及北方地区能调动的部队悉数调到了京师附近勤王,还是连通州都没能守住。
直至到了京郊,凭借重炮和马队的优势,才遏止住了北窜长毛的攻势。
若是短毛发逆北窜京师,会是怎样一番境况,咸丰甚至不敢细想。
“回主子,奴才觉得现在不宜分兵襄樊。”肃顺直言道。
“眼下正值雨季,我大清内河水师不如短毛发逆,雨季南下攻襄樊,乃以我之短,击短毛发逆之长。
我大清之于短毛发逆,马队乃我大清所长,即使要南征襄樊,也当以入冬之后,河水封冻,土地坚硬之时南征襄樊为宜。
奴才以为,当务之急应当集中兵力,肃清京郊的长毛发逆,以稳定京师,乃至天下的人心。”
肃顺也清楚襄樊的重要性,他又何尝不想早日克复襄樊,但肃顺不认为在雨季南征襄樊是什么好主意。
操之过急只会适得其反。
再者,比起襄樊的远虑,京郊的近忧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。
眼下京郊的战事正处于关键阶段,现在抽调兵力南征襄樊,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,顾此失彼。
“如若短毛以襄樊为跳板北上,同北窜的长毛合并一处,该当如何?”咸丰道出了他的担忧。
“短毛用兵图稳,短毛不会在没有万全的准备下贸然北窜,再者,有乌兰泰、骆秉章、张亮基、江忠源等人在长沙牵制短毛,短毛不敢大举北上。”肃顺说道。
历来关于长毛、短毛的战报肃顺不仅都看过,还让人整理装订成册,以便时时查阅。
故肃顺虽远在京师,没有亲临前线,但他对长毛、短毛都有一定的了解。
长毛和短毛用兵风格说是两个极端也不为过。
长毛用兵激进,短毛用兵稳重,喜欢稳扎稳打。
肃顺认为以短毛的作战风格,不会在准备不充分,有长沙清军威胁后方的情况下贸然北上,长驱直入攻打京师。
清军在南方战场,尤其是湖湘战场表现得一塌糊涂,但北方战场的主动权,仍旧在清廷这边。
“传旨,速速肃清剿灭京郊的长毛,务必在入冬之前结束京郊的战事。”咸丰凝思良久,终于做出了决断。
与此同时,京师城东郊的北伐军大营。
因处于前线战区之故,为了防止被清军集中兵力突破,五万余太平军在京师城东郊扎的是品字形大营,各营之间互相呼应。
如此布营增加了纵深,使得清军难以破营,即使偶尔被清军破了一两个营地,整个东郊大营也不致全线崩溃,尚有补救的余地。
当然,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,那便是牺牲了营地的正面宽度,难以对京师城这等规格的城池形成合围。
韦昌辉、林凤祥等人不是不想将营寨拉长,对京师城完成合围,而是实在做不到。
除却留守通州、东安、武清、天津等不得不守的城池,后方能抽调的兵力基本都被韦昌辉、林凤祥抽调到了前线。
李开芳曾提出直接将所有兵力押到京师城下,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建议。
不过韦昌辉没有采纳。
五万人围不住的城池,七万人未必围得住,更改变不了他们兵力劣势的现实。
再者,南方的老兄弟基本都已经被抽调到了前线,多增加两万余北方新兵,能起到的作用也极为有限,改变不了战局。
去年韦昌辉已经吃了不少没有后方的亏,入冬以来一路忍饥挨饿,减员甚多,今年韦昌辉不想在这方面栽跟头,故坚持留守天津,为自己,也为北伐军留了条后路。
京师城东郊的中军大帐内,辅王韦昌辉眉头紧锁,目光落在大帐中央粗糙的沙盘上。
一侧的李开芳双手抱胸,凝视着帐外灰蒙蒙的天空,一言不发。
帐外传来的连绵不绝的铳炮声令他心烦意乱。
“又退下来了!”
随着帐外的铳炮声渐歇,帐帘猛地被掀开,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和血腥气随之涌入帐内,林凤祥大踏步走了进来,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愤懑。
“弟兄们冲了三次,都被清妖的铳炮给压了回来!僧格林沁和胜保的马队在侧翼游弋,我们的弟兄只要冲锋阵型稍微一散,他们的马队就冲上来放箭,没有足够的炮火压制,根本靠不近城墙!”